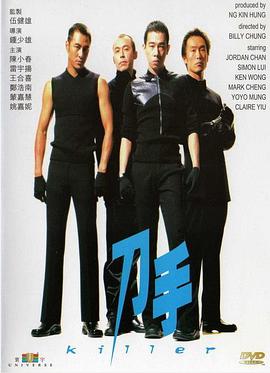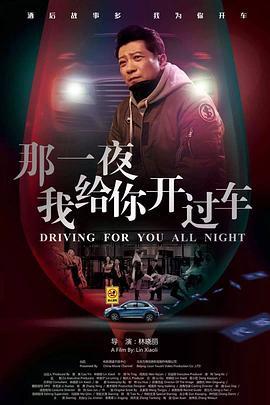@《天使在美国第一部:千禧年降临2》相关热播
@最近更新剧情片
@《天使在美国第一部:千禧年降临2》相关影评
(写于2017.11)上个月我去高雄电影节看了加菲主演的NTlive版《天使在美国》。去看aia完全是机缘巧合。我是加菲的屏幕粉,与其说视他为偶像去追求,更像视他为优秀的艺术家去欣赏。不追他行程,所以完全不知道aia会在台湾放。我留意高雄电影节是因为张震,他的作品在期间放映,他本人也会去现场站台,然而等到我上官网看排片时,人家已经全部播完了!造化弄人啊!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看接下来的排片,就在茫茫片海中看到了aia。像做梦一样。我知道这场戏在美国一票难求,别说现场了,即使是NTlive版要在中国看到也很难。作为一个生活在厦门的贫民窟女孩,如果不是因为高雄电影节,我可能一辈子都无缘看这场戏。我浑身过电,泪盈于睫,当下只有一个念头:来不及了快买票……多亏了台湾线上付款程序之繁琐,等我弄完七七八八的信息时,头脑已经冷静下来。上FB随手一搜,就捡到了今年最大的便宜——有人在二手主页出票,两天上下场,原价一张800NT,现在两张900,我当场尖叫!一波三折,就是这么搞定了我的高雄一天两夜豪华云恋爱之旅。我之前不了解任何《天使在美国》的内容,只知道加菲演一个艾滋病患者,联想片名,起初以为是一部抗艾励志片,因为从国内社交平台流出的各种资源看,画面里的加菲总是穿着一身病服,眼睛有光,活灵活现,笑容温暖治愈,乍看还真是天使。然而等我迷迷瞪瞪地过完这两晚,至今已过一个月,看了各路老师的评论,仍然不知道如何描述这部戏。它足以载入史册。故事从一个美国犹太人的葬礼讲起,有着女巫一样的弯勾鼻的牧师(我不知道犹太传统里给死者祝祷的人物叫啥)念了一串希伯来风味英语,关于宗教传统、移民历史等等,对于亚伯拉罕一神教一知半解且互相混淆的我,ok,宗教,这是第一道坎。舞台场景一转,第二道坎接踵而来。James McArdle饰演的路易(我认为全剧最幸福的人,先睡加菲后睡小狼),就是死者的孙子,和同性爱人普莱尔坐在长椅上聊人生。这个人神经兮兮的,可能是个搞哲学的,大谈里根治下的美国与理想国的辩证关系——我听不懂。第三个场景发生在臭名昭著的律师罗伊的办公室,听他骂完一串荡气回肠的脏话,一旁小狼演的摩门教徒乔忍不住了:朋友,你能不能不要在god后面跟fuck。两人谈话时,罗伊老是在乔背上画圈抚摸(太gay了!)这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社会上层律师是同性恋,并且垂涎着年轻可口的乔皮特。这一幕的信息量同样让我头大,什么保守党,什么社会科层制,什么摩门教,我都不知道啊!!!第四幕是乔家里,妄想症的妻子哈珀老是怀疑夫妻的床下有人,歇斯底里地发疯,渴望有小精灵带她去南极看臭氧层漏洞。然后墙上真的出现了以时空旅行为业务的人。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是场下智商最低的人,这段哈珀的独白里牵扯到社会学、哲学、还有地理,我统统懵逼。总之,开头二十分钟,我气还没喘匀的时候,连甩到我脸上的四个包袱,足够奠定了我对全剧的看法:厉害死你。主要角色陆续出场后,线索开始分明,我自己理出三条,不一定对,我并没有看明白这部戏,而且已经过了一个月,记忆难免有偏差。一是围绕着两个同性艾滋病患普莱尔和罗伊,他们身边的路易、乔、黑人变装皇后护士和乔的妈妈汉娜和鬼魂。二是普莱尔得病后出现的各种幻觉:Prior Walter是个古老的名字,可以追溯到英国中世纪时期,被病痛折磨时,他开始幻想其他普莱尔来找他,有拿着镰刀的死神,提着灯的老人。还有天使,经过一次一次的拷问和告解,最后从天使那里得到解救。应了片名,天使在美国。三是哈珀与普莱尔两个神经病的脑电波交流。哈珀的第一次妄想里就出现了变装花冠女王的普莱尔。这两人从没有在现实里会过面,但人不可能凭空想象出一个全新的人,一切都是现实的映射。忘了戏中的谁说,大致意思是自己以为从无聊现实中制造了一个有趣的幻境,其实幻境何尝不是源自无聊的现实。两个被恋人背叛的可怜人,一个得病后被恋人抛弃,一个得知丈夫是同性恋,巨大的煎熬让他们在妄想的场域里互相开解。最后也是他们俩上了天堂到此一游,普莱尔得到救赎,回到人间,迎接千禧,而哈珀就不得而知了。信息量之丰富、复杂和深刻让本咸鱼目瞪口呆,宏大叙事、魔幻现实以及社会批判,每个词都足够一个资质平平如我的人钻研一生,而我竟然如此幸运,在这么少不经事的年纪里看到一部融合了这一切的文艺作品,我不知道别人在看这部戏的时候是什么心情,但是我,在很多时候的某一秒,有如神谕降临。论体力消耗,加菲绝对是全卡司里排名第一的一个。我在台下看他充满女性特质的小动作、看他歇斯底里的发疯、声嘶力竭的求饶,额上的青筋和哭太用力冒出的鼻涕泡都清晰分明,心里既为他鼓掌,也为他担忧。我能喜欢上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是多么骄傲的事,而又担心这种浸入式演法让他被困在角色里出不来。普莱尔这个角色太费心神了,虽然结局雨霁天青,但过程中的生理疼痛、情感煎熬和精神折磨并不是好消受的,就像林黛玉之于陈晓旭,未免让人唏嘘。第一晚看完从影院出来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半,沿海的公路灯火通明,尽管沿街商铺都打烊了,但车来车往,依然没有午夜的感觉。我大着胆子一个人走在路边,前面两个女士,三十出头,讨论着刚刚结束的片子。我记得很清楚,其中一个女士说,电影中出现的grace其实是恩典,字幕翻译成高贵,可见译者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宗教背景的。她的声音也好听,低柔,文静,娓娓道来。我当时想,等我三十岁的时候,是不是也可以像她一样,那么优雅地和朋友欣赏和讨论一场自己喜欢的艺术家的表演。第二场那天是周日,台北在举行彩虹游行,而高雄上班族在当晚举行万圣节趴。凌晨地铁已经停运,我徒步回美丽岛。这条路有4公里,我怀着满肚子感慨走在公路上,说不清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,狂欢告一段落的男男女女们在酒吧门口说笑,穿成变装女王的老外、浓妆艳抹的男护士、打扮成恶魔的少女,就像他们从刚刚散场的电影里走出来一样,从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美国走到21世纪的台湾,与此同时,我的朋友圈全是结束了一天游行的朋友们的感触。我不知道这种情况算不算伪道德主义,毕竟我是认同“当一个人说我不歧视LGBT的时候,他已经在歧视了”的,不过至少我能说,那一刻,我们是同样的自由的灵魂。我喜欢加菲的时间不长,今年六月考试周太无聊,找了《超凡蜘蛛侠2》出来看,和记不清情节的第一部截然不同,高中时我还觉得这个蜘蛛太丑了,脸太长,五官奇奇怪怪的,而两年后,几乎是一瞬间,这张脸给我“生命之光、欲望之火”的冲动,只凭着这张脸,我就可以想象和他恋爱、上床。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,所以他是特别的。荷兰弟版小蜘蛛出来后,我看过有人批评《超凡》里感情线太突兀,恋爱、分手、复合都像嚼快餐。我不认同。让这样的一个彼得帕克用湿漉漉的眼睛凝视你,细细软软的嗓音念你的名字,任谁是格温斯黛茜都受不了吧。暑假在家补了《血战钢锯岭》和《社交网络》,越来越觉得这个男人耐看。我会一直记得,穿着吊带西装裤的少年,在提琴协奏的背景乐里被镜头拉到我眼前,那是我已有认知里所能想象到,30年代美国少年最好看的样子。